-
首页
-
- 首页
- 观点
姚洋:苏格兰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启示
发布日期:2018-07-10 12:4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说到启蒙运动,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法国,很少有人会想到苏格兰。在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之前,苏格兰是欧洲的边陲穷国,人口也只有100多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穷乡僻壤,却在18世纪涌现出了一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家,并引领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高光时代,苏格兰的高光时代无疑是工业革命的100年。苏格兰是如何做到的?亚瑟·赫尔曼的“How the Scots Invented the Modern World”(《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回答了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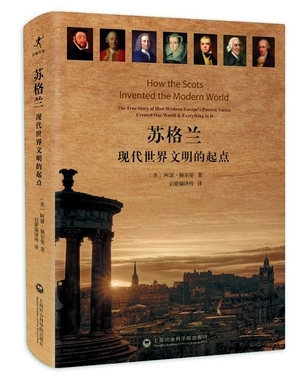
(《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美)阿瑟·赫尔曼著,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8月)
对人性的再认识在1707年合并之前,苏格兰和英格兰两个国家分分合合上千年。自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被伊丽莎白女王确定为继承人之后,苏格兰与英格兰共享同一个君主100年。17世纪的英格兰,尽管饱受内战的蹂躏,但现代化的曙光已经降临,不仅产生了牛顿、霍布斯和洛克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而且还产生了近代工商业。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格兰更是进入商业大发展时期,海外贸易迅速扩张。苏格兰人感觉被挤压,但几次和英格兰在海外的贸易争夺都以失败告终。面对困境,苏格兰的选择不是和英格兰进行无休止的争斗,而是与英格兰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在当时,合并的动力来自于苏格兰对贸易收益的渴望,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苏格兰从此走上了一条引领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康庄大道。这条大道的起点是对人性的再认识。
人性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思考人类社会的起点。霍布斯是第一位确立个体在哲学分析中的地位并把人性作为理论起点的思想家。霍布斯长寿,活到91岁,这个年纪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是耄耋之岁。但是,与同时代以及稍晚期的思想家一样,他并没有意识到英国17世纪的动荡对于英国、乃至世界的意义;相反,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的处境:政局动荡,灭顶之灾随时可以降临,为躲避战火,许多人、包括霍布斯自己不得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动荡之中,霍布斯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斗,进而,他所参悟的人性就是自私和占有欲。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类就会陷入“人与人作对”的丛林社会,人的生命因而变得“孤独、贫困、污浊、野蛮和短暂”。但是,这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状态,为此,人们应该签订一个契约,把他们的自然权利让渡给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由它来维持和平、抵御外敌入侵。
但是,这种从个体直接到国家的解决方案,既可能导致真正的“利维坦”式独裁政府,也忽视了社会这个中间环节可能发挥的自组织作用。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们补上了这一环。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的学说是这一环的起点。他的原名叫亨利·候姆(Henry Home),“凯姆斯勋爵”是他成为苏格兰大法官时才获得的以他的家乡命名的爵号。
与启蒙运动同步,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起始于对绝对宗教信仰的批判。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是苏格兰第一个挑战绝对基督教教义的人。在他那里,人的道德感不再是上帝赋予的,而是人生而俱来的本性。对于刚刚跨入现代化门槛的苏格兰来说,这个观点具有革命性,但是,相比于霍布斯的理论,这个观点显然是落后了。凯姆斯勋爵的学说是对霍布斯和哈奇森的中和。一方面,他赞同霍布斯对自然人性的描述,认为“占有欲是自然赋予人的秉性”;另一方面,他又借鉴了哈奇森的观点,认为社会本身蕴含“良知的声音”。法律对于秩序是必要的,但只有当法律和社会良知一致的时候,社会才进入一个完美的状态。那么,人类社会是如何演化并接近这个完美状态呢?为回答这个问题,凯姆斯勋爵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这四个阶段是: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和商业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个体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没有社会,因而也不需要法律;到了农业阶段,社会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即“个体的劳作不仅让自己得利,而且也让他人得利”。此时,新的职业不断产生,人们不得不诉诸合作来完成日常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由此,法律有了用武之地,社会也因此朝着“融洽的亲近关系”发展。
但是,这种亲近关系才刚刚开始,它的高潮是商业社会。此时,交换更加频繁,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收益,同时也产生新的观念和习性。斯密的好友、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的总结,代表了那个时代苏格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对商业社会的肯定态度:
商业会消解那些维持国与国之间差异和敌意的偏见;它缓和并滋润人们的习性;它用世间最强烈的关系之一——满足共同需求的欲望——把国家连接在一起。在每一个国家,它为全体公民建立一种秩序,以满足公民维护公共安宁的渴望,从而给各国带来和平。当商业精神在一个社会开始上升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社会的政策、国际联盟、战争和谈判里发现一个新的灵魂。
近代商业产生于荷兰和英格兰,但仅仅是商人逐利的手段,是人类占有和改善生活的自然秉性的延伸;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在于为商业赋予了一个公共目的,将之升华为人类进步的阶梯。然而,要维持商业的繁荣,一个自由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凯姆斯勋爵的门生、也是他的堂弟大卫·休谟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在《论公民自由》一文里,休谟断言:
商业只能在自由政府中繁荣,这种观点已成定论;而且似乎⋯⋯有着更悠久、更广泛的经验基础。⋯⋯在我看来,商业易于在绝对政府中衰落,不是因为那里缺乏安全,而是因为它不够体面。君主国必然需要等级臣属关系来维持。出身、头衔和地位的荣耀必然超过了勤劳和富有;一旦这些观念盛行,所有巨商都会受到诱惑,放弃经商,而去购买那些特权和荣誉的职位。
为市场经济找到伦理基础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本身就是自由社会的推动者。告别宗教束缚的苏格兰,具有它的南部长兄英格兰所没有的一个优势,即不存在明显的社会等级。在地理上,苏格兰分成南部丘陵地带和北部高地两部分。在18世纪,苏格兰高地仍然处在凯姆斯勋爵所定义的游牧阶段,农奴制度(serfdom)是它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南部丘陵地带以农业为主,但商业已经成为两座主要城市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主要经济活动。相较之下,格拉斯哥的商业气息更加浓厚,它的海外贸易,特别是来自于美洲新大陆的烟叶贸易让它成为当时英国首屈一指的富裕城市。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则更加具有人文气息,18世纪中叶涌现出一批知识分子俱乐部,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制造场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754年成立的“选择学会”(The Select Society),它囊括了当时爱丁堡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而凯姆斯勋爵是当仁不让的中心。
他把几乎每个晚上都耗费在晚宴活动上,而且也经常是餐桌上话题的主宰。他的话语如同他的长相一般坚毅,语气里总是带着一丝苏格兰式的嘲讽——对所有事务持批评的态度,但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从最接地气的“常识”出发,用一种调侃却不失体面的方式说出来。
“常识”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所共同遵守的一个底线原则,这把他们和欧洲那些专注于形而上学的启蒙思想家们区分开来。今天,我们常以苏格兰经验主义来总结苏格兰启蒙运动,但其中略微带有一丝贬义,似乎认为,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没有理论,因而不如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先进。然而,历史经验证明,欧洲大陆思想家们的理论构建往往成为人类社会动荡和苦难的催化剂。
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它的后果需要法国花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得以消化;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框架里,马克思发明了剩余价值学说,引领欧洲阶级对垒数十年;接下来,斯大林在苏联发明计划经济,走上一条被哈耶克批判的“通往奴役之路”;最为甚者,尼采这位疯子发明超人理论,最终成为纳粹反犹主义运动的思想源泉。人类需要超前于现实的理论构建,但是,欧洲19世纪以降的痛苦历史告诉我们,理论家最好是保持一种对现实的谦卑态度,否则,灾难可能就在前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最大优势就是现实主义。当他们的大陆同辈们忙于发明社会改造理论的时候,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则严肃地研究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伟大成就——商业社会——兴起的原因和运行逻辑,而斯密的《国富论》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当中的集大成者。
《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但在1798年被爱丁堡大学的著名学者杜加尔德·斯图亚特(Dugald Stewart)开讲座介绍这本书之前,斯密对于绝大多数爱丁堡人而言都是陌生的,更遑论伦敦的人们了。不同于大多数同时代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斯密居住在格拉斯哥,而不是爱丁堡。年轻时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稍后(1750年、1751年)在爱丁堡所做的讲座给了他足够的名声,让他获得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个伦理学教授职位,从此在格拉斯哥安顿下来。但是,启蒙运动的核心在爱丁堡,格拉斯哥的作用还要等工业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才充分显示出来。斯密参加了选择学会,因而时常坐上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之间的邮车奔走于两座城市之间。两城之间区区75公里的距离,那个时候单程却需要一天半的时间,但足以让斯密在第二天中午到达爱丁堡,下午和晚上会晤朋友、参加聚会,然后第二天返回格拉斯哥。爱丁堡之行总是让斯密有所斩获,他在《国富论》里所表达的思想,如社会分工和市场的规模效应,都已经在其他人、特别是凯姆斯勋爵的学说中有所体现。斯密所做的,是系统性地揭示商业社会的运行规律,弥合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两条主线——哈奇森的人生而具有道德感和凯姆斯勋爵的人天然地具有占有欲——之间的张力。
在写作《国富论》之前,斯密写了《道德情操论》。此时的他,多少还受到哈奇森的影响,但又试图有所发展。为此,他区分了伦理的两个层次,一个是正义,另一个是同情心,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感。道德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此时,斯密还是在追随哈奇森。道德给社会增添色彩,但是,就社会的运作而言,正义就已经足够了。从否定面向来说,正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肯定面向来说,正义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因而,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 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做出劝戒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此时,斯密的学术天平已经倒向凯姆斯勋爵了,开始为《国富论》奠定伦理基础。跟随凯姆斯勋爵的论断,斯密把自己理论的出发点设定在劳动分工。一国的产出取决于国民的劳动,而劳动的效率取决于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效率。斯密用针扣生产为例说明分工的好处。如果一个人来做针扣,恐怕他一天连20个也做不出来。但是,在针扣工厂里,小小的针扣被分成数个工序来进行生产,拉丝、取直、剪切、削尖、打磨等等,每个工人专注于一个工序,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一个工厂每天可以生产几千枚针扣。
劳动分工成为工业化大生产的标志,至20世纪初,福特发明流水线作业,把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推向顶峰。但是,分工不仅主宰工厂内部的生产过程,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主要推动力。分工促进交易,而交易又反过来促进分工;如此,社会产出的提高,不需要求助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切,而是可以来源于每个人的利己之心。动物需要博取同类的欢心才可能得到同类的帮助,而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不可能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刺激别人的利己之心而自愿替自己做事,他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目的。任何一个想与别人做买卖的人,都可以先这样提议:请把我所要的东西给我吧,这样你就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按照这个办法,可以取得所需要的大部分帮助。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供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恩惠,而是因为他们自利的打算。
人天然地具有占有欲,但这并不一定导致霍布斯的丛林,通过市场交换,人的占有欲可以成为提高自己和他人福利的源泉。由此,斯密为市场经济找到了伦理基础。但这不是《国富论》的全部内容;斯密在书中还详细讨论了价格、工资和利息的形成过程,资本积累以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问题,为现代经济学搭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到19世纪后半叶,门格尔等人发明了边际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瓦尔拉斯构建了一般均衡理论,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完整的描述。边际革命让经济学获得了“庸俗”的头衔,但是,边际分析让经济学掌握了数学分析工具,从而开始了系统的进步。而这一切,都起始于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表达的思想。
脚踏实地的改良者苏格兰知识分子为商业社会建立了伦理基础,接下来就是苏格兰实干家们的舞台了。如同他们的理论一样,务实和理性构成了苏格兰人性格的底色。苏格兰人也许不是最好的发明家,但绝对是优秀的技术改进者。“就像他们没有发明科学,或资本主义,或进步和自由的理念一样,苏格兰人也没有发明多少技术。”但是,他们却善于改进现有技术,让它们变得为日常生活所用。神奇的是,从“有用”的小处着手,苏格兰人对技术的改进却成为推动英国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最重要力量。
苏格兰对现代技术文明的贡献始于对医学的改进。在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大学里的医学院只教给学生医学理论,不鼓励学生与病人之间有任何身体接触,更别提给病人开刀了,因为这些工作是专属仆人或剃刀师做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与之不同,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把他们培养成医学通才。学院开设解剖课,把手术从一个剃刀师才愿意干的脏活变成了一个基于解剖学和生物学之上的科学门类。爱丁堡大学培养的医生在整个英国名声鹊起,它的医学院也成为大不列颠想成为医生的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地方。许多苏格兰医生成为英国有钱人的御用医生,但这没有妨碍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公共卫生做出贡献。其中之一是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他是用柑橘治疗坏血病的发明者。
林德建议英国海军在舰艇上常备柑橘,但没有得到响应,只有詹姆斯·库克船长——一个有着苏格兰血统的探险家——在1769年开始他的澳洲探险时才听从了林德的建议。直到1795年,柑橘才成为英国海军舰艇上必备的食品,而这还要感谢另外一位苏格兰人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ne)爵士对英国海军的劝说。大英帝国能够称霸世界海洋,小小的柑橘功不可没。
对工业革命贡献最大的苏格兰人当属詹姆斯·瓦特。流行的说法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实际情况是,瓦特只是改进了蒸汽机,让它变得更加实用。蒸汽机是两位英格兰人托马斯·纽克曼(Thomas Newcomen)和托马斯·萨维里(Thomas Savery)发明的。瓦特听说这个机器的时候,只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名工匠,帮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教授做一些实验工具。他们俩从1763年起开始研究蒸汽机的改进。老式的蒸汽机只有一个带活塞的气缸,活塞连着一根铁杆,蒸汽进入气缸推动活塞上行,后者压低铁杆做工。但是,活塞下行要等蒸汽自然冷却,耗时很多。瓦特的目标是让活塞快速运动起来。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在1765年春天一个晴好的午后,当瓦特外出散步的时候,灵感降临:如果给气缸连上一个真空容器,蒸汽就会自动排出到容器里,从而实现了活塞的循环运动。到1775年,瓦特和英格兰著名的铁器锻造家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合作,开始了长达几十年对于蒸汽机生产的垄断。自此,人类跨入了工业社会。
瓦特这个励志故事的奇妙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文盲。他改进蒸汽机,没有得到多少科学的指导;他也不关心背后的科学原理,只关心如何让这部神奇的机器更加有用。这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态度,却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
苏格兰人对工业革命的贡献远不止于英国境内。自打并入英国之后,苏格兰出现几次移民潮,尤以向北美的移民居多。在美国早期建国的历史中,苏格兰人就发挥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普林斯顿大学是苏格兰移民建立的学校,开创了美国综合性人文教育的先河,直到19世纪后半叶哈佛等大学开始引进德国的分科教育之后,才慢慢失去优势。苏格兰人以其固有的务实精神,引领了美国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在19世纪前半叶,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地区是美国技术工人的最大来源地,到19世纪中期,苏格兰妇女也加入到工业劳动大军之中。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苏格兰人更是在工业界大显身手,贝尔和卡耐基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人。
贝尔在爱丁堡长大,并在爱丁堡大学接受教育。他的家庭以设计和制造语音设备出名,这为他后来发明电话创造了条件。相比于贝尔,卡耐基的发家史更像一个苏格兰人“应有”的样子。他于1835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纺织小城,他能记住的第一个声音是他父亲纺车发出的“吱呀”声。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家庭纺织作坊被工厂所取代,卡耐基一家于1848年移民美国。像其他苏格兰移民子弟一样,卡耐基小小的年纪就必须参加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电报公司的投递员,但是,他聪慧过人,很快就学会了电报的翻译,甚至能够从电报机的“滴答”声里判断电文内容。这让他很快得到上司的信任,成为主管。他的第一桶金是在内战期间用铁路为北方军队运送军用物资,到内战结束时,他已经拥有了40万美元的财富。
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财富?卡耐基看中了当时最先进的行业,钢铁。为此,他回到英国学习钢铁制造技术,回到美国之后,他建立了从铁矿石和煤炭的开采到钢铁产品销售的一体化公司,并以苏格兰人所特有的精打细算压缩成本,在40年的时间里,主导了美国的钢铁业。1901年,他把公司卖给J. P. 摩根,获得4.8亿美元。此后,他专心慈善,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800多个公共图书馆。他也关心教育事业,但不是一般化的教育,而是“有用”的教育,相信“知识如果只是用来玄思,就没有任何价值”。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耐基—梅隆大学以工程见长,不是没有道理的。
苏格兰人的触角也延伸到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用一艘军舰“复仇女神号”就完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黄埔守军。这艘军舰是苏格兰造船师在利物浦建造的。它长56米,由两座60马力的蒸汽机推动,装备两门32磅大炮、五门6磅小炮和一座投掷器。在它面前,清朝海军的木壳船就像火柴盒一样不堪一击。当然,苏格兰人对中国所做的,也不都是做大英帝国侵略战争的帮凶;他们的商业才能也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比如,汇丰银行就是苏格兰人托马斯·萨瑟兰德(Thomas Sutherland)于1864年在香港发起成立的,1865年在上海开业,成为中国较早开始运作的现代银行。
苏格兰人也许不善于进行颠覆性的发明,但他们凭着对“有用”的追求,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技术进步。苏格兰哲学相信人类的知识来自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而知识是否可靠,“有用”与否是唯一的检验标准。人类文明是人类建构的结果,但不同的建构方式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大体而言,从经验出发、以“有用”为目的,大概是最安全、而且也常常是最有效的方式。
何处安放乡愁?如同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苏格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面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在与英格兰合并的头半个世纪里,苏格兰爆发了多次起义,其中尤以174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最为严重,影响也最为深远。光荣革命终结了来自苏格兰的斯图加特王室在英国的统治,但是,被流放的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家人并不死心,试图从汉诺威王室手中夺回政权。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儿子查尔斯王子从意大利潜回苏格兰,在苏格兰高地东海岸登陆并组建军队,向南部进军。当时的苏格兰高地仍然处于地主家族主导的农奴制度下,不仅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就连地主们也过着勉强果腹的生活,和苏格兰南部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查尔斯王子的到来,唤起了部分家族对旧日苏格兰秩序的憧憬,他们领着各自的佃农参加查尔斯的军队。
但是,这么一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根本不是英国军队的对手,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边界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溃败回高地地区。英军乘胜追击,在高地大开杀戒,屠戮了无数同情詹姆斯党的民众。1745年变成了苏格兰高地永远的一块伤疤。但这还不是高地人民困难的终结,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圈地运动,让大多数高地佃农失去了土地,被迫南迁,许多人移民海外。苏格兰精英奠定了美国早期的高等教育体系,而普通苏格兰移民也在美国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独立战争因殖民地民众反抗英国的不合理税负而起,但不是所有殖民地的民众都愿意脱离英国。吊诡的是,来自苏格兰高地的移民就属于这类人。他们加入英国军队,和华盛顿的军队作战,而他们的主要对手,恰恰是来自于苏格兰南部的移民,后者是美洲独立的坚定支持者。本来希望斯图亚特王室复辟的苏格兰高地人民,为什么要支持当政的汉诺威王室呢?合理的解释恐怕只有“乡愁”二字。
在决定与英格兰合并之时,爱丁堡的精英们之间出现过巨大分歧,英国皇室为此准备了巨款来贿赂其中的反对者。民众反对合并的情绪也很强烈,他们不仅经常上街支持议会里的反对者,而且还袭扰支持合并的议员。苏格兰议会从1707年10月开始,对先前英国方面提出的合并条约逐条投票。几位强烈支持合并的人士以娴熟的政治手腕和雄辩的口才赢得了多数议员的支持,最终,条约的最后一项条款于次年1月7日通过。英国皇室的贿赂款没有派上用场,都被中间人中饱私囊了。合并给苏格兰南部带来显著的好处。爱丁堡迅速崛起,人口大幅度增加。像绝大多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一样,爱丁堡老城本来就拥挤和肮脏,迅速增加的人口加剧了这个局面。市政当局因此决定在城市北边修建新城。爱丁堡的有钱人纷纷用新获得的财富在新城建设宽敞的住宅,其中也包括像休谟这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
格拉斯哥的商业发展比爱丁堡更迅速。由于合并,苏格兰的商人现在可以享受和英格兰商人同等的待遇,获得海外贸易的特许权。格拉斯哥涌现出一批专做美洲烟叶贸易的商人,他们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苏格兰南部很快就融入英格兰经济体系之中。到18世纪下半叶,整个苏格兰很少有人再质疑合并的合理性了。不仅如此,苏格兰精英们纷纷自觉地“英格兰化”。休谟和斯密的英语都不太好,但是他们坚持用英语写作。爱丁堡的精英们关心的不是苏格兰的事务,而是整个英国的事务;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爱丁堡成为英国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和公共舆论中心。创刊于1802年的《爱丁堡评论》,主导英国公共舆论数十年的时间,直到1929年才停刊。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文章,是英国知识分子成名的象征。在苏格兰本土,年轻人向往伦敦的生活,许多人在那里获得良好的发展,其中还出了几位首相。苏格兰人的身份从“苏格兰”变成了“不列颠”。
但是,乡愁不会轻易消散。在18世纪、19世纪之交,当绝大多数苏格兰人热情拥抱他们的“不列颠”身份的时候,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用他的诗作和小说唤起了人们对苏格兰高地旧日生活的浪漫想象。在他之前,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于1762年发表长诗《莪相》,声称这是他在民间收集的凯尔特游吟诗人莪相的盖尔语诗作,从而在苏格兰掀起一股怀旧浪潮。然而,很快就有人指出,这不是莪相本人的作品,甚至不是民间盖尔语诗作。最终,经过认真研究,爱丁堡高地协会于1805年宣布《莪相》为伪作,大多数诗篇是麦克弗森自己直接用英语写的。但是,《莪相》所带来的怀旧风并没有停止,而且,因为司各特的诗作和小说变得更加强劲。
出生于1771年的司各特患有小儿麻痹症,但这不妨碍他拥有浪漫主义情怀。他不喜欢剧烈的社会变革,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甚至组织了一支骑兵部队,参加英国抵抗拿破仑扩张的战争。趁着做地方官的机会,他游历苏格兰和英格兰边界地区,收集各地的民歌,最终于1802年至1803年出版三卷《苏格兰边区歌谣集》。随后,他的历史长诗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享誉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拜伦的出现让司各特意识到,他接着写诗歌没有什么前途了,转而开始写历史小说。在当时,小说是给下等人看的,上不了大雅之堂,因此,司各特一开始是用笔名发表小说的。他的最著名的小说是《威弗利》(Waverley)。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的原型是在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被平息之后,最后护送查尔斯王子出海的麦克唐纳家族的女主人芙洛娜·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而男主人公是虚构的一位英军军官威弗利。小说的基调是悲壮的。
芙洛娜是失去的苏格兰高地生活和秩序的化身,而威弗利是英国现代化进程的化身。威弗利本来的任务是捉拿查尔斯王子,最终却被芙洛娜的美丽和高贵品格所征服,自己也变为一个詹姆斯党人。现代化的大势不可阻挡,但是,苏格兰高地的精神不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沉淀为司各特笔下凄美的想象。这种想象最后以一种近乎滑稽的方式在1822年英国国王乔治四世造访爱丁堡的时候完美落幕。
拥抱世界,还是回归自己自打詹姆斯一世离开苏格兰之后,200多年间,没有一位英国国王造访过苏格兰。浪漫主义文学激发了全英国对苏格兰的浪漫想象。就像当今中国重新发现婺源这样的农村一样,英国兴起了苏格兰旅游热;在节假日,通往苏格兰高地的大路上挤满了马车,载着朝圣般的观光客驶往他们心目中浪漫的苏格兰。受此感染,乔治四世希望访问爱丁堡,而司各特被请来策划迎接国王的大典。乔治四世希望看到纯粹的苏格兰文化,这和司各特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要把国王的访问当作一次复兴苏格兰高地文化的契机。
为此,他设计了苏格兰高地游行,让游行的队伍按照高地习俗打扮起来。问题是,就连司各特自己也不知道苏格兰高地是如何着装打扮的。好在国王也不知道苏格兰高地人该如何打扮,司各特可以尽情地发挥他的想象,最终选定格子裙为游行队伍的着装。在此之前,所谓的格子裙,不过是高地穷人拴在身上的一块遮体的粗布而已,现在却要成为庆典服装。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集结来自高地的游行队伍。经过圈地运动的驱赶,苏格兰高地早已变成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后,实际参加游行的队伍是由爱丁堡人组成的。国王到达爱丁堡的那天,30万人,也就是苏格兰人口的七分之一强,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这场想象出来的高地文化的复兴大戏。自此,长期被视为野蛮人穿着的苏格兰方格裙成为时髦服装,精明的商人们还为不同的高地家族设计了不同式样的格子裙,就连英国军队中来自苏格兰的旅团,也开始把格子裙作为他们的正规服装。就这样,男人穿格子裙,成了苏格兰的民族风俗。
然而,苏格兰高地文化的复兴,也仅仅到此为止。在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以及20世纪前半叶里,苏格兰的文化基调是融入英国。无论是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还是不列颠本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苏格兰人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然而,任何美好的因缘似乎都会有褪色的一天。
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间隙,起始于“二战”之后。1950年的圣诞节,四位苏格兰大学生从西敏寺的爱德华宝座下偷走了命运之石,并把它运回苏格兰。命运之石是过去的苏格兰国王加冕用的,1296年被入侵的英国国王夺走,并用于后来的加冕仪式。偷走的命运之石很快被寻获,并被英国警方运回西敏寺,放回到爱德华宝座下面。这段插曲,开启了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大幕,背后却是苏格兰地位的下降。
随着日本、德国以及其他赶超国家的兴起,英国工业不可阻挡地走向衰落,作为英国工业重镇的格拉斯哥等苏格兰城市也因此衰落;另一方面,从前苏格兰人引以为豪的职业,如医生,被来自印度等国家的移民所占领。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兴起,与其说是因为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觉醒,毋宁说是因为英国不再像十八九世纪那样,能够激发苏格兰人的热情。1996年,英国把命运之石运回苏格兰,安放在爱丁堡城堡里。然而,这样的示好并没有浇灭苏格兰独立的火花,进入21世纪反倒呈愈演愈烈之势。英国鲁莽的脱欧行为,再一次把苏格兰独立运动推向前台。英格兰的经济基本上被伦敦所主导,而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脱欧并不会影响伦敦的国际地位,所以也不会太影响英格兰的经济。苏格兰则不一样,和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仍然是支撑其经济的重要支柱,苏格兰人不愿失去欧洲。英格兰对苏格兰人的吸引力本来就在下降,脱殴更是强化了这个趋势。苏格兰的乡愁找到了新的载体,在经济上和英格兰分道扬镳。
人类文明是有周期的,主导力量是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涨落。
农耕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经历一万多年,最终在唐、宋时期的中国达到高峰;工业文明发源于西欧,目前还在扩散的过程之中。在这个大周期运动中,各个国家或地区又有各自的小周期,因而,欧美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上升期—高光期—稳定或下降期”的全过程。苏格兰在工业文明即将兴起的时候,搭上了英国现代化的列车,并在工业化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上升期和高光期在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工业文明的扩散,英国的地位下降,连带把苏格兰的地位也拉了下来。
回首苏格兰的历史,我们仿佛听到苏格兰既忧伤又高亢的风笛声在时空中飘过。忧伤来自苏格兰高地挥不去的乡愁,高亢来自全体苏格兰人坚韧的性格。拥抱世界,还是回归自己,仍然是苏格兰悬而未决的事情。
(2018年3月8日完稿于朗润园。姚洋/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文首刊于2018年5月2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