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10年第009、010期(总第874、875期)简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20次报告会快报通稿
发布日期:2010-02-28 10:4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20次报告会于2010年2月27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本次报告会侧重讨论交通设施建设、气候与低碳经济、美国经济近况、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等问题。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郭小碚、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宋国青、胡大源和卢锋分别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
会议主持人卢锋教授根据第19次“朗润预测”汇总结果,用四句话概括22家特约分析机构对2010年第1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增长重回快车道,通胀又进预警期,外贸提速顺差减,息口微调有预期”。以下为六位主讲人演讲内容概要。
郭小碚:交通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
围绕交通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郭小碚所长演讲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交通运输中综合运输的基本认识;二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三利用经济危机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综合运输是交通运输发展的科学理念,指的是以消耗最少的社会资源满足运输需求。综合运输体系指综合发展和利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管道等运输方式,按照各自的技术经济特点,形成网络布局合理、运输工具高效低耗及组织管理先进的交通运输综合体,实现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整体经济性。
自1949年以来,中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很大成就,郭所长按照历史脉络分三个时段介绍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第一个时段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三十年间中国铁路、公路、内河运输线路里程快速增长,运输网布局显著改善,并初步形成了交通运输工业体系。客、货运量在这一时期分别增长了14和45倍。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运输能力与经济社会的运输需求矛盾突出,表现在乘车难、托运难上。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交通运输形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在国家主要运输大通道框架初步构建、运能不足现象开始缓解、交通运输需求从数量向质量转变。
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初到2010年的“十一五”末。这一时期铁路、公路、长输油输气管道里程及机场、深水泊位数量均大幅增长,交通运输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2008年汶川地震后很短的时间内全国物资人员能充分调动,也说明了交通运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能力仍存在一些局部不适应,服务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比较大。
中国的交通运输系统正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首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加快发展时期,许多已批准的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原本设想在2020-2030年之后建成,现在看来都会提前、甚至在“十二五”期间完成。其次,交通运输系统正处于从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建设向运输服务系统建设转变时期,如“零换乘”、“无缝衔接”等等。第三,促进交通运输引导经济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城市交通设施建设中引导城市布局及产业结构,这在今后会是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具有投资规模大、范围广、周期长及带动相关产业作用明显等特点,郭所长的观点是,利用经济危机时期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短期内提振经济、保障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则是提高运输供给能力,改变交通运输的滞后状况。譬如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重点是公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开始在这一时期加速发展。2009年为应对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交通基础设施为1.5万亿元。2009年,交通基础设施实际投资约2万亿元,比2008年增长48%,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10.63%,它的短期效果明显,作为应急措施效果显著。
最后,郭所长总结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三大方面:一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能降低运输费用,稳定物价并促进土地开发;二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可以降低经济成本,提高区域资源范围。三是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可以扩大贸易范围,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对城市化进程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李远芳整理)
胡大源:气候变化应对与低碳经济
胡大源教授的讲演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回顾;二是影响政府气候变化对策的因素;三是我国能源发展与减排承诺;四是公众意愿与气候变化问题的不确定性;五是企业应对策略。
首先,自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 建立以来,世界各国开始了多次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其中1990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为后来气候谈判及设置减排目标的参照系,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就以其为参照系对发达国家设置减排目标,同时提出三种灵活调节机制,即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排放贸易、联合履行机制,以及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清洁发展机制。
然而《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执行却不尽如意。以2006年与1990年对比发现,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16%,成为减排表现最好的发达国家,但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及加拿大却不降反增,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200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增加了152.8%,凸显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压力与空间。近期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再次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纷纷做出减排承诺,“基础四国”(BASICs,指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也提出减排目标。但一些欠发达国家关注“适应”(adapt)问题,希望获得更多援助。
其次,影响政府气候变化对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各国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收入阶段对环境问题的评价及科学研究成果与媒体宣传。其中,各国面临的具体情况包括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气候变化对本国的潜在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公众的感受与意识、地域性环境治理问题。与常见环境问题不同,气候变化这一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未来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全球性长期影响,并存在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各国的具体情况差异决定了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差异性。欧盟经济成熟,新能源技术先进,人口下降,能源需求相对稳定,减排优势明显。美国则提出要以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公开透明为附加条件,即排放的“可量度、可报告与可核实”。“三可”不仅将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为偿还历史排放债务而应承担减排义务置于同样标准之下,而且会限制自身为了发展和脱贫而必须的排放空间,短期内不具有可操作性,但长期来看却是一个趋势。
第三、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污染物排放高,可再生能源价格高和稳定性差,未来发展离不开国家有关扶持政策。关于我国的减排承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实现这个目标不是特别困难,关键靠核电。二是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以2005至2008年每年平均下降速率3.33%推测至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39.8%。此外,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即煤炭比例下降,石油、天然气上升,核电及可再生能源上升至15%,碳排放强度可以下降10%。
第四,气候变化的公众意愿发生显著改变,气候变化问题出现不确定性。Nielson与牛津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在2009年10月全球调查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表示担忧的人数比重由2007年的41%下降到2009的37%。基于2006-2009年美国公众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及独立人士中相信全球变暖有确凿的依据的比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与公众意愿下降的现象相似,民众对气候科学家研究的信任也出现显著变化,其中气候门事件引发公众质疑IPCC的公信力。2010年1月IPCC正式承认,其2007年发表的气候变化第4次评估报告中存在重大“失误”,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2007年Green和Armstrong通过对IPCC发布的全球气温变化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分析,评估其预测方法及步骤,发现至少违背了72项长期预测的准则。
最后关注企业应对策略,以两个例子来说明。据《新世纪周刊》近期报道,比亚迪做电动车,其竞争力并不仅仅是前沿新技术,而是中国劳动力优势发挥到极致所创造的特定生产研发方式。资本市场上比亚迪可能已透支了新能源概念,有关投资风险也需要关注。另一个例子是万科大楼,其“漂浮的水平杆状”设计解决了创新与使用功能间的关系,不但降低能耗而且增加了景观绿地,还有利于空气流通;独具一格的斜拉桥式悬索建筑结构降低了建设成本;内部装修多用竹制材料,不但费用低而且新颖别致;可动式外遮阳表面既美观又可降低能耗;万科大楼的建设融合了多项节能减排新措施。总而言之,做各种形象宣传,大家都可以做,关键是如何把绿色概念用于降低企业成本,从而保证企业和经济将来可持续发展。企业发展应用环保理念能否成功?降低成本方可持续。
(陈建奇整理)
卢锋:奥巴马元年美国经济透视
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临危受命,宣称将锐意变革“再造美国”。奥巴马元年经济施政可用“一个中心和三项改革”概括。一个中心是通过实施ARRR法案刺激经济,三项改革包括医疗、金融、能源-气侯政策改革。总额8780亿美元ARRA法案到2009年底约已支出35%,此外还实施“现金换旧车(CARS)”项目、拓展延长ARRA条款等以刺激经济。
美国危机救助政策收到初步成效。各种利差持续下降和低位企稳,2009年三、四季度GDP增长由负转正,股指2009年初反弹和三种房价指数先后跌幅收窄或企稳回升,说明美国经济已走出急救室并呈现某些复苏形态。事实证明美国经济具有抵御危机打击的调整能力,然而美国经济要想重回景气增长还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克服以下四方面困难尤其关键。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危机前美国增长模式深层问题在于,给定现有汇率、工资等国际相对价格体系,美国企业难以在国内找到足够数量具有竞争力投资项目,追求高增长势必过度依赖消费。从数据看,战后60年消费平均对总需求增长贡献79%,投资为22%。2001-2009年消费贡献率高达112%,意味着经济增长以投资、净出口负增长为前提,显然无法持续。美国去年三季度增长主要靠消费,四季度增长主要靠存货降速收窄,复苏能否持续关键在固定资产投资。
二是“两个10%的矛盾”。美国失业率2009年10月上升到10.1%。与美国战后十次复苏通常同时伴随失业率走低不同,目前失业率仍处10%高位。美国朝野主张加大刺激力度加以应对,但是巨大财政窟窿对长期增长带来更大风险。2009年美国赤字1.42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9.9%,联邦债务率也上升到83.4%仅次于二战峰值高位。高失业率要求加大赤字刺激力度,高赤字率要求尽快重建财政平衡,“两个10%”显示美国经济被疗效相互冲突并发重症所困扰。
三是负信贷增长与通货膨胀矛盾。危机导致信贷大跌,此次信贷下跌程度为五十年之最,目前仍是负增长。没有信贷回升,就不能有活跃投资,难有持续复苏,也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然而同时通胀压力已悄然再现。今年元月美国CPI、PPI、进口价格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9%、6.3%、11.6%。这说明美国复苏面临内部结构困难,也说明本轮危机特征在于,并非通过美国复苏带动全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增长,而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强劲复苏,率先推动美国进口价格上涨,一定程度推高美国物价。美国面对经济增长乏力与通胀压力上升尴尬局面。
四是外部失衡可能卷土重来。金融危机爆发后,严重衰退使美国外贸逆差显著收窄。然而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伴随外部失衡“复苏”。简单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如果经济结构未能得到调整,假定201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和4%,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例将上升1.0和1.5个百分点。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历史数据,有理由认为美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所下降。过去6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2%,但2001-2009年年均增长不到2%,2002-2007年景气期增长率也只有2.8%。考虑前一段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未来面临结构调整困难,可推测除非发生特别有利的重大产业革命,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显著下降。具体降幅可进一步研究,作为初步推测可认为未来十年平均水平不会超过2.0%-2.5%。
应对深层矛盾,美国面临两类选择。一类是追求短期速成治标策略,一类是致力于结构调整的治本策略。速成策略基于“高失业率—GDP缺口—需求刺激”认识范式,试图通过超级刺激政策和几次立法改革跳出困境。政策特征在于忽视退出过迟和赤字扩大风险,试图采用债务货币化-通胀方法为未来财政危机解套。涉外领域诉诸保护主义转移矛盾,甚至冒险采取更为激化矛盾方式释放压力。
与速成治标策略不同,致力长期结构调整治本策略需要正视深层结构问题,接受一个时期潜在增长速度降低现实,在低增长低通胀宏观环境中培育市场力量进行结构调整。同时把控制财政赤字、遵守货币纪律、应对通胀风险置于优先地位,严肃对待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义务。最后需要培育技术创新、谋求前沿突破、拓宽全球产业技术可能性空间,把美国相对优势建立在生产力创新上。
认识美国对我国开放宏观政策调整具有借鉴意义。我国自身经验证明总需求并非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从客观情况看外部经济也无力支撑中国总需求增长,我们要对内需增长足以提供合意总需求这一判断树立信心。其次,中国不仅在大宗商品投资上是增量大国,去年开始在总需求指标上成为增量领跑国家,面对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深刻变化,我们需要以汇率-利率政策调整为重要内容,尽快建立适应开放型大国经济需要的宏观政策架构。最后,在以我为主进行政策调整基础上,反对美国的保护主义,鼓励美国进行深层改革。
(王健整理)
李迅雷:2010年中国经济走入偏热区间
李迅雷先生围绕2010年中国经济走入偏热区间的问题阐述四方面观点。一是讨论美国经济下半年强于上半年的经验证据;二是说明中国经济将步入“过热区间”的基本观点;三是解释中国长期增长的动力与障碍;四是评论政策调整问题。
首先,美国经济有望出现前低后高的增长态势。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两次复苏路径来看,企业投资复苏滞后经济复苏1年左右,本轮美国经济复苏始于2009年第3季度,美国企业投资有望从2010年第3季度开始强劲增长,由此预计2010年美国投资将实现平稳交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5%左右。其中上半年投资依靠存货拉动,下半年投资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此外,从历史数据看,消费实际增速与失业率变动息息相关,如果失业率在2010年下半年下降,那么消费在第三季度增速可能达到5%。当然,消费超预期加之美元走强,意味着美国的出口部门在2010年可能重现对经济增长负贡献。然而,总体而言,预计2010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在存货扩张支撑下将保持3%左右增长,而下半年在企业投资扩张、失业率下降、消费上升刺激下将达到4%以上增长。
其次,美国经济增长超预期,中国经济将面临过热风险。我们估算美国经济如增长1个百分点,将提升中国出口增长率10%,按照上述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预计2010年中国出口增速可能达到30%左右。另一方面,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贡献了92.3%,创30年来历史新高。2009年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在2010年仍将保持较高的增幅。当然,在私人投资仍不够活跃的情况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将受制于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投资的增长,但公共部门的投资对信贷依赖更强。预计2010年货币供应量增速为19%,新增贷款量将达到7.6万亿元左右,与此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大概是28.39%,预计2010年中国GDP增速将达10.5%,其中消费贡献4.5个百分点,投资贡献5个百分点,出口贡献1个百分点。因此,2010年GDP增速将处于10%以上的过热区间。
第三,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既有动力也有阻力。城市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化将推动重工业化快速发展。重工业化自2009年下半年起再度加速,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与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将会有所下降,但仍会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仍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力,但出口增长速度很难明显高于全球出口平均增速,这一阶段可能会维持10年左右。然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也存在明显阻碍因素,未来中国有人口老龄化、教育医疗等问题,还有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社会收入差距的问题,经济增长是好事,但它还有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体现在收入差距的恶化。
最后是政策调整问题探讨。我国从1995年开始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外延的扩张到内生的发展。这些都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效果如何。我们的研究发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没有带来GDP的同比增长,而中国东部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投入产出比都是比较低的,最有竞争力的还是珠江三角洲,投入产出比在4倍左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因而,我们不能够只讲调结构,应该关注如何改体制。
(陈建奇整理)
宋国青:目前有轻度通胀倾向
宋国青教授主要讨论两方面问题:一是M1增长剧烈波动及其原因,二是当前通货膨胀等方面情况。
首先讨论M1增长变化情况。1月份M1同比增长39.7%,超过过去十年平均增长率两倍。尽管1月信贷较多对此有贡献,但在贷款增量不大的去年下半年,M1同比增长率持续上升,11月达34.6%。
M1主要是现金与企业活期存款,相比包含储蓄存款的M2,在短期有更强的活动性。过去有评论观点把储蓄存款叫作“笼中的老虎”,M1就可以看作是走到了笼子门口的老虎。市场流行观点把M1相对M2更高的增长速度称作剪刀差,认为它对通货膨胀具有更强预测性。如果用目前这个指标水平预测下一步通货膨胀,情况会非常严重。上一次40%的M1增长率出现在1994年,当时通货膨胀率高达20%。
宋教授从两个角度对上述流行思路提出不同看法。一是换环比指标看,情况没有那么严重。M1和M2的环比增长率在2009年1季度达到顶点后下降,并在下半年大幅度下降。这提供了一个同比增长率与环比增长率反向变化的例子。看环比的话,去年3月M1增长率比今年1月要高,“老虎”要出笼的话,去年3月就在笼门口了,但没听见叫几声,又回去了。
二是对M1相对M2的增长率变动原因提供一个不同解释。他首先列举了影响M1增长率三方面因素:一是信贷货币总体增长,二是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比例变化,三是企业存款中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比例变化。用季调后M1相对M2比例可以控制信贷货币总体增长对M1绝对增长率的影响,并刻画M1相对M2的增长率波动。这一指标在2004年以前相对稳定,2004年后出现大起大落。2007年底达到上一个高点,2008年底降至最低点,2009年至今再次上升。
M1相对M2比例上升有可能是企业把定期存款变成活期存款。如果真是这样,企业部门在紧缩货币的时候把定期存款变成活期存款,对于关注控制货币扩张带来通胀危害的货币当局而言可以说非常友好!不过,考察居民存款相对M2比例发现,这一指标和M1相对M2比例有明显反向关系。可见M1相对M2比例大幅波动,主要是M2中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比例变化引起,主要不是由企业存款内部结构变动所导致的。
进一步看,影响居民和企业存款比例的最主要因素是住房销售。上一次居民存款比例低点在2007年10月,正是房屋销售的高点。后来房屋销售下跌,居民存款比例上升。2009年以来,房屋销售猛涨,居民存款比例随之减少。居民密集购买住房,将其持有的储蓄存款大量转变为企业存款,其中大部分成为活期存款并计入M1。
对居民而言,买房是将其所持有的货币资产转变为房产,总资产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从个人消费函数角度看,影响个人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总财富或总资产,资产结构的影响小得多。因此,居民买房导致居民存款减少,却不会减少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居民买房导致企业存款增加。企业存款特别是活期存款增加则会增加企业需求。因此,居民房产、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后两者即为货币)共同决定总需求。从这一角度,可以把个人持有的房产加入货币之中,构成更广义的货币。
住房销售与M1相对M2比例的关系具有两点含义。第一,2009年上半年信贷猛增但是住房销售低迷,下半年信贷增速减缓然而住房销售火爆,住房销售与信贷扩张之间这一反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稳总需求的作用。不过这只是偶然之事,如此剧烈信贷波动今后不宜重复为好。第二,股市波动与住房销售的关系并不总是一致。因此,尽管根据信贷和住房销售可以很好地预测M1,却难以利用来预测股市。
接下来讨论当前通货膨胀等问题。2009年12月CPI环比大幅上涨后,1月份有所下跌,2月份基本持平。过去半年CPI增长折年率2.8%,是比较温和的通胀水平。去年第4季度特别是12月高通胀主要由天气异常所致,出口强劲增长也起到一定作用。总的来说,总需求过度引起的通胀压力并不大,2009年信贷增长对CPI的冲击已经充分释放。
今年贸易顺差很可能增长,平衡总需求要求投资增长率比上年下降。通胀与货币关系将恢复到2008年以前状况。考虑住房销售疲软的紧缩效果,1季度信贷增加2.5万亿可能轻度偏多,但不严重。未来货币供给需要结合出口和住房销售情况进行调整,全年增加7万亿贷款也许略微多一点。最后,目前形势下利率调零点几个百分点本身没有实质性的作用,至多有象征性的意义。
(刘鎏整理)
周其仁:向下调整的困难——对2010达沃斯论坛的感受
周其仁教授于1月27-30日参加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本次演讲中,周教授从他对达沃斯论坛的观察和感受出发,引出当前发达国际经济复苏中普遍伴随的高失业率问题。就这一问题,他着重从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大势的角度阐释了其根源、表现、未来发展及对中国的含义。
周教授在对达沃斯论坛众多研讨会的观察中发现,实际统计数据所呈现的世界经济图像与各界人士的感受“不容易加得起来”。一方面统计数据显示,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全球经济出现了实际的复苏和经济增长,国际组织预测结果、采购经理指数(PMI)及各主要股指也均显示了广泛的预测向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金融业。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祸首”的金融业在达沃斯论坛上又陷入了“限薪”的争议。金融业的奖金甚至比危机前更高。“限薪”要求说明金融业从政府救市、零利率和低利率政策中获利颇丰。这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经验完全不一样。
另一方面,达沃斯论坛上西方政要及各界名流对经济的感受却普遍不好,主流意见是不能轻言衰退已经结束、经济已经复苏,尤其是对经济刺激政策退出问题讳莫如深。IMF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调高对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同时IMF总裁Kahn在发言中又认为复苏进程脆弱而不均衡,退出方案的时机选择面临困难。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Summers的说法是: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正在复苏,但亲身感受它还在衰退之中。论坛上,韩国总统李明博、Stiglitz教授、三年前在达沃斯预言了危机的Roubini教授及芝加哥大学的Rajan教授等人也都表现出对复苏脆弱的担忧。
为什么在发达经济的实际增长状况与主流感受及判断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周教授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经济虽然出现复苏与增长,但还面对严重的失业。美国失业率仍高达10%,欧元区失业率9.8%,最高的西班牙甚至达到18%。这一情况下,“主权债务危机”被达沃斯首日全球经济讨论小组“选”为全球经济最大威胁,可没有人敢说退出。
更进一步,为什么发达经济体会经历“无就业增长的复苏”?周教授把这一现象与冷战后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联系起来。他把这一格局形容为“两个海平面的世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是一个高海平面,它们之间贸易相互往来并形成分工结构,所以是打通的。它们的人均收入很高,人数也很少。中国、印度这些原来走自力更生、计划经济道路的国家是一个低海平面。它们人均收入很低但人数巨大。两个海平面差距非常大,按国际劳工组织计算,1980年中国工人制造业小时工资仅是美国工人同期工资的1%,这两年可能也不到10%。
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印度从九十年代开放、1991年前苏联解体,上述两个海平面之间开始逐步打通。由于制度文化上的差异,开始打通的时候流量很小。随着低海平面制度成本的下降及学习曲线的提高,这个通道越打越大。但是,这个通道并非所有要素都可以流通,产品、资本、信息的流动远远大于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发达经济的资本总体上在流向低海平面国家,以结合当地更便宜的人工。发达国家到低海平面国家就业的人也来了一些,但数量很少。由此出现的天下大势是,高的往下,低的往上。这释放了全球新的比较优势的巨量势能,并引发全球产业布局重组、经济结构变动以及利益关系调整。
周教授进一步用“通而不平”来概括目前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征。“通”带来全球化的利益,发达经济得到了廉价产品,这对消费者来说是高兴的。但因为仍然“不平”,对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者带来麻烦甚至提出挑战:工资怎么往下调?这是目前这个世界的一个实质性困难。
发达国家向下调整比发展中国家向上调整要难得多,社保体系更为健全的欧洲又比美国在调整上更为艰难。这一过程会带来很多摩擦、麻烦和冲突。达沃斯论坛上,法国总统萨科奇很反常地痛斥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并声言“那些故意压低本币汇率的国家迟早要被保护主义痛击”。这句话里至少包括中国。虽然保护主义早已经名誉扫地,想搞保护主义的人也不提保护主义,但有可能有比保护主义更麻烦的事情。找茬、一点小事闹成国际头条新闻情况会经常出现,这种“热闹场面”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一形势下,中国的“十二五”期间能不能有类似过去五年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周教授从达沃斯回来后觉得要打一个问号。相应的,中国人有两个选择:一是人为维持低的海平面,这会对发达国家很不利,对自己实际也有麻烦;二是让低海平面因应经济基本面演变适当升得快一些,这对我们自己有利,对发达国家也有利,因为后者往下调也就相对容易一些。那么,怎么让中国的低海平面适当升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需要把汇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外需内需平衡等相关议题,都放到“通而不平”的国际大环境下来做思考。
(李远芳整理)
主会场 
郭小碚 
胡大源 
卢锋 
李迅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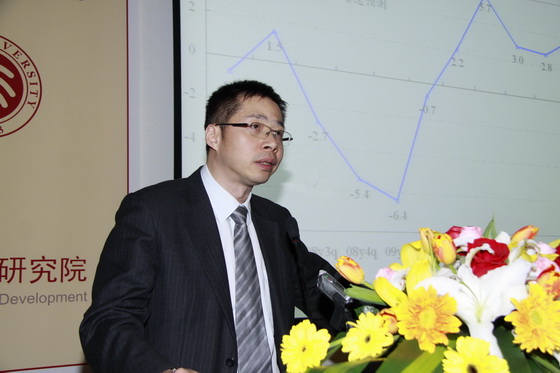
宋国青 
周其仁 
主会场 
主席台 
主席台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